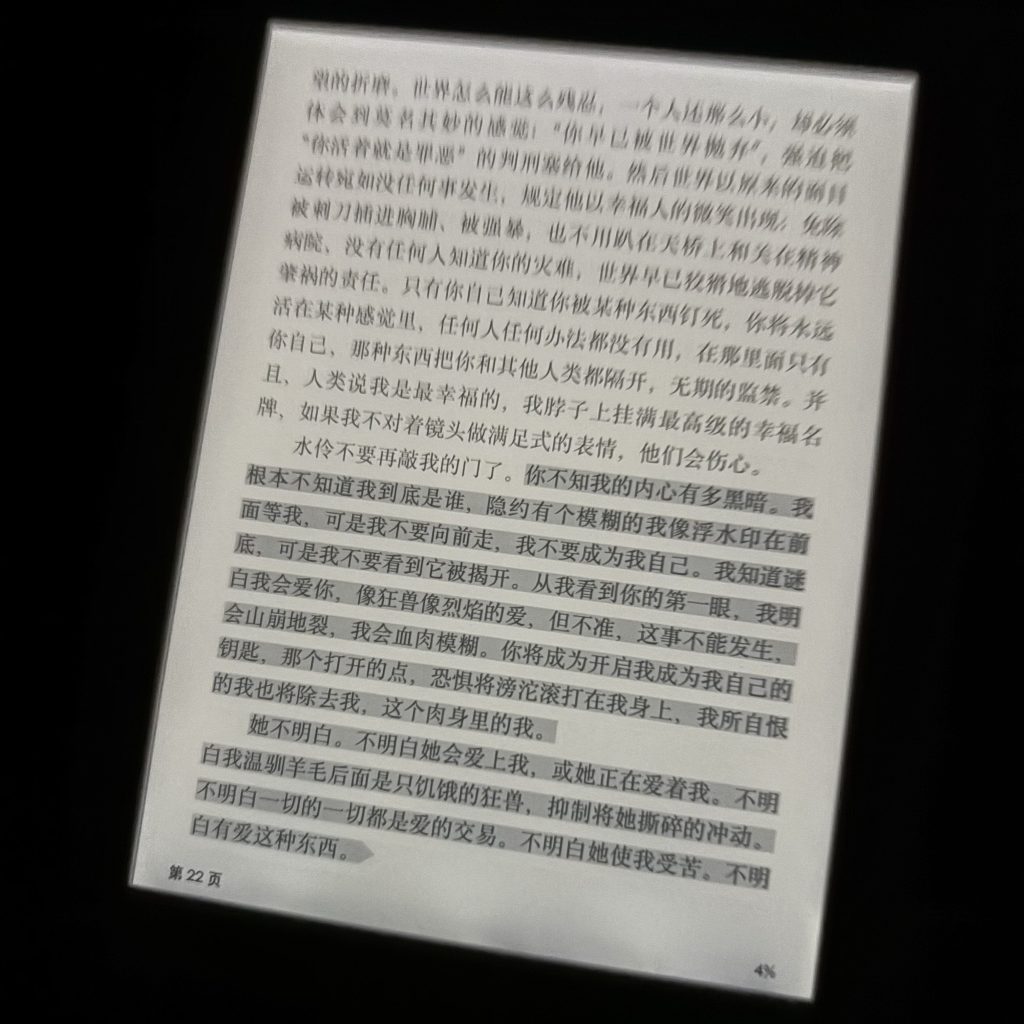
2025.2.4
兩年前我在鹽田千春個人展的時候,我與這位我第一次聽説的藝術家產生了某種微妙的共鳴:人與人之間就像她作品中的紅綫一樣,總是在不停地相交與分離。沒有兩個人是永遠平行的,也不會有人永遠停留在交點。其實這一點我早在四年前就有所體會。那年我十七歲,而如今我已邁進了我的二十年代,可我仍舊懼怕別離,不論是誰。
那晚她問我我們之間相遇的概率,我説是二分之一也是八十億分之一。相遇與否的確只會有兩種情況,但就命運而言,這種概率趨近於零。我多少是相信命運的,所以很多時候我感覺我們很幸運,有時也會覺得我們緣分還未盡。可命運就是這樣,你永遠不知道兩個人何時會有交點,何時會再次相交,何時這一切都隨風而去。我們就這樣度過了一禮拜,但直到今日我們仍然不知道我們現在是怎樣的一種關係,或者説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希望的樣子是什麼。所以照我說,還是那晚我同她所講的“敦偉大友誼”。我覺著這個詞特別有意思,至於我們的未來是否會像王二與陳清揚一樣,那都是後話了。
我們絕口不提愛情,但我們做遍了有關愛情的一切。這不重要,我們都知曉愛情並非我們所追求的,當下若是開心,若是幸福,那便就足夠了。很多時候沒有必要將一件事情剖析得過於仔細,我們既然能在一年後再次拾起這一切,那多少也説明我們是認可對方的。此刻就是我們的第二個交點,我無法得知我們是否還會有第三個第四個,也許不再會有,所以我仍會對此感到恐懼。於是我開始嘗試忘掉未來,握緊此時我所擁有的一切,有關她的一切。
我似乎聽見了海豹的呢喃伴著海風襲來,遙遠得像深海裡鯨魚的悲鳴。現在是凌晨三點三十九分,我感受著她一呼一吸閒的熱浪,而她就這樣靜靜地注視著我。
2025.2.25
未來這些年,我想我會一直與數字打交道。這並非危言聳聽,幾年前的我怎樣也想不到有一天我會踏入理科專業。事實上我的文科也並不優秀,可以說是半斤八兩——高考語文我甚至都沒有及格,但應試教育下的語文和真正的文學還是有著天壤之別的。我清楚地知曉這並非是我理想中想要的,但愛好止於愛好,生存需要這般無趣的手段。
來到這裡我前後換了四次專業,從電影跨越到數學,猶如千禧年前後社會變遷般的跳躍。人終究是多元的,興趣並不意味著一輩子都要囿於其中,就像我仍在寫作,但這無法成為我生存的手段,畢竟在生死存亡之際,愛好總是次要的。
2025.2.27
現在是凌晨一點四十六,我再一次緊鄰崩潰的邊緣。這是沒有緣由的。我曾試著尋找原因,進而盡可能地避免,但其深處是空無一物的、毫無道理的。既然無端而起,也就無避免之談。
距今已有六年之久,改善並不算大,偶爾我仍在體會剝開肌膚的那種釋放感。在度過這近乎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後,我對一切的起點早已模糊,是家境、學業、還是母親?我不再會知曉了。曾有很多人問我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感覺,但一直無法找到合適的形容,現在我知道了:這是一種身體無法承負個體靈魂的悲哀。當一個人真正意識到自我與他人的不同時就會陷入這種困頓——我仍未從這種困頓中脫離出來,於是慢慢地轉變為一種身體的記憶,或是習慣。
我的身體無法承受我靈魂的重量,也無法承受分離的痛苦。仔細想想,其實自我們出生起就在不斷地學習什麼是分離,以及怎樣面對分離。身邊的人不斷地在改朝換代,從學齡前到大學畢業乃至工作以後,人群就像水流一般,而我站在漩渦中心,任憑其衝刷著我,而我卻不能做分毫。有些離別是短暫的,而有些卻是永恆的,沒有人知道這次分手後究竟是何種,所以我總是不斷地在焦慮,不斷地恐懼未來所擁有的一切可能。前些日子想起糯米和飛,心又在隱隱地抽動。我想人生就是不斷經歷這種無力感,當失去達到某種閾值,生命也就隨之消逝。
人是永遠無法理解一個人的靈魂的,就像鄭曾說過的那樣:“我感受不到你的靈魂”,可這又有誰能感受到呢?我之所以是我,是因為我與他人的歷史並不相同,靈魂是歷史的具象化,而人是無法體會自己未曾經歷過的一切,就像我也無法感受到鄭的靈魂一樣。
現在是凌晨兩點二十二,酒杯見底,我想起一些久遠的夢,而明日依舊是工作日。

Leave a Comment